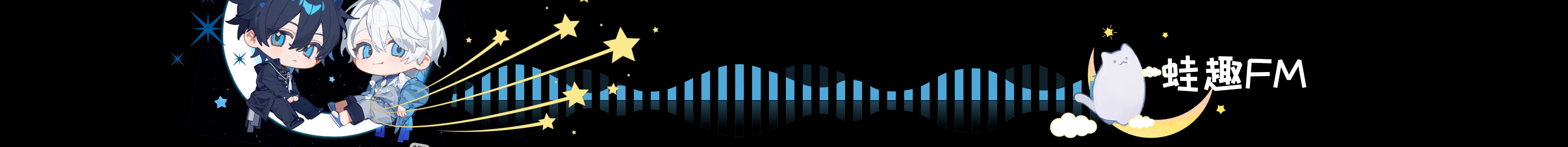湿漉漉的雨夜,实习医生沈砚在回家路上捡到只受伤的垂耳兔。当他用绷带缠好兔爪时,指尖突然触到温热的肌肤——浑身湿透的少年蜷缩在沙发里,发梢还沾着草叶,头顶软绵绵的兔耳随着呼吸轻颤。这个自称"阿绒"的男孩总用湿漉漉的眼睛追着沈砚转,直到某天沈砚发现,阿绒偷偷用毛爪按着他落在枕间的银丝眼镜发呆。
"你捡到我的时候,心跳声比雨打树叶还吵。"
"人类的体温是三十七度,可你掌心的温度烫得能烘干我打结的绒毛。"
"要是在春天告白,你会不会像喜欢蒲公英那样喜欢我?"
"嘘,别碰耳朵...那里、那里是求偶期才会给人摸的......"
暮色漫过诊疗室的百叶窗,阿绒踮着脚在医药柜前找葡萄糖。沈砚刚做完手术推门进来,就看见少年腰间松垮系着自己的白大褂,细瘦脚踝从过长的衣摆下露出来,随着翻找动作在光影里晃成两道瓷釉。
"沈医生要补充糖分吗?"阿绒转身时撞落两盒棉签,兔耳慌乱地抖成绒团,"他们说人类累的时候......"
话音被突然拉近的距离截断。沈砚单手撑住他身后的柜门,消毒水气味混着少年发间若有似无的青草香,指腹擦过对方唇角的葡萄糖粉末:"这种时候,补充糖分有更直接的方式。"
阿绒的耳朵瞬间充血变粉,尾巴球在衣摆下炸成蒲公英。他闭上眼睛的刹那,窗外玉兰树被晚风撞得簌簌作响,惊落十七片带着体温的花瓣。